信以载魂:湖湘红色信笺里的百年精神坐标
张立云
近日,收到湖湘青年才俊刘宝钦赠阅的《湖湘红色书信》,心情格外激动。该书由张志初、刘宝钦联合主编,湖南人民出版社和中共党史出版社联合出版。据悉,该书从筹备到出版历时六年,直至今年6月才正式与读者见面。好事多磨,这般长时间的精心打磨,无疑是对老一辈锲而不舍革命精神最恰如其分的传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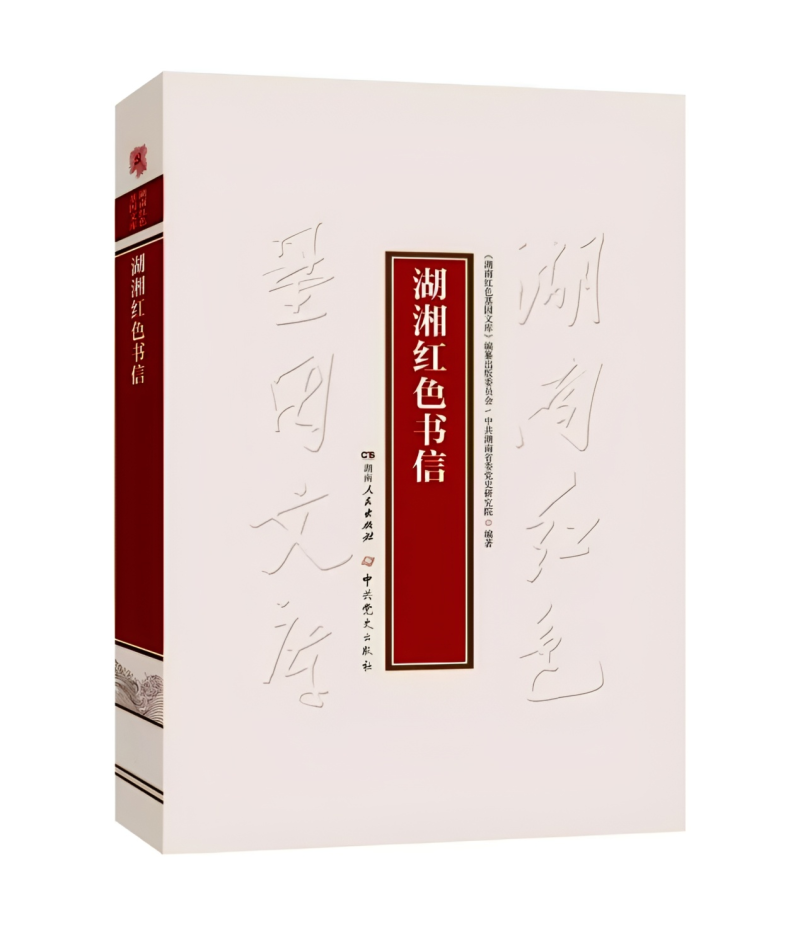
一
人类文明的进步,始终伴随着文字传递方式的演进。从甲骨刻辞承载的原始讯息,到竹简绢帛记录的文明脉络,书信自始至终都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重要载体。从两河流域的泥板文书,到中国古代“鱼传尺素”的浪漫,书信不仅是信息的传递者,更是文明的见证者。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倾诉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学抱负;陆游以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”的诗笺传递教子之道,书信早已超越单纯的实用功能,成为精神传承的重要媒介。曾几何时,书信亦是国人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与人际交往工具:古时借驿站、烽火传递讯息,后来信鸽、邮差成为连接远方的纽带。家人收到远方来信时的激动、恋人接过滚烫情书时的甜蜜、陌生朋友因书信相知相交的欣喜,皆是书信时代独有的温暖记忆。
随着时代发展,通信方式从手写信演变为网络邮件,再到电话、手机、微信等工具普及,纸上书写情感的时代渐渐远去。这究竟是文明的进步,还是某种精神载体的失落?如今的我们已鲜少提笔写信,00后们更是几乎没有通过信使传递情感的经历。信使,这位曾穿梭于街巷的温情使者,虽已淡出日常,却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。所幸,老一辈留下的信件中,仍藏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整理并出版这些书信,正是对这份珍贵精神财富的珍视与传承。
二
当指尖轻轻抚过《湖湘红色书信》的红色书脊,仿佛能触到百年党史的脉动。这部典籍以泛黄信笺为舟,载着湖湘儿女的赤诚之心穿越历史长河。当中国近代史的烽火燃遍湖湘大地,书信这一古老文体被注入全新灵魂:书中收录的207封红色信札,将其升华为镌刻信仰的精神丰碑,在书信文化日渐式微的当下,照亮了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。
这些信札,堪称书信发展史中最璀璨的红色坐标。陈毅安在战壕里写给妻子李志强的54封家书,既有“烽火连三月”的战地纪实,更有“革命成功日,痛饮庆功酒”的浪漫期许。那些写在卷烟纸、公文背面的文字,打破了传统家书的私域边界,让个人悲欢与民族命运紧紧交织。
与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的闲逸不同,夏明翰1928年3月在狱中写下“甘愿抛头颅,洒热血”的绝笔,字字如钢刀刻下革命者的初心;不同于曾国藩家书的治家箴言,向警予1923年1月6日致父母的信中,“儿亦当格外奋发,兢兢业业以图成功于万一耳”的誓言,重构了传统孝道的时代内涵。这些书信延续了中国文人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,更将其升华为“信以载魂”的革命史诗。
从历史角落发掘整理的红色书信,自带鲜活的时代注脚。杨开慧藏在墙缝中的手稿,墨迹虽已斑驳,字句却能穿越历史长空。1982年整修长沙板仓杨开慧故居时,人们在卧室后墙离地面约两米的泥砖缝中发现了它,这份尘封半个多世纪的思念与坚守才重见天日。1929年3月,她在致堂弟杨开明的信中坦陈:“我总觉得我的颈项上,好像自死神那里飞起来一根毒蛇样的绳索”,却仍坚定表示“说到死,我并不惧怕”。这份柔弱中的刚强,恰是革命者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;而“藏信于墙”的细节,恰似对古代“鱼腹藏书”的现代演绎,让书信成为连接个人命运与历史进程的隐秘纽带。
“楚虽三户,亡秦必楚”的血性,在湖湘大地孕育出独特的红色基因。《湖湘红色书信》以书信为棱镜,将这份基因的内涵尽数折射: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情怀,是“实事求是”的务实品格,更是“敢为天下先”的革命勇气。信笺中的家国情怀,在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的抉择中愈发炽烈;实事求是的精神,则在字里行间自然流淌,成为湖湘儿女代代相传的精神密码。
三
风云激荡的岁月里,无数湖湘儿女以笔为刃、以信为灯,在字里行间书写信仰与担当。今天的我们翻开这些书信,仍能从中汲取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。
这份力量,究竟该如何融入当下的生活?
首先是穿越历史烟云仍熠熠生辉的信仰之力。百年前的湖湘大地,革命先烈们或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灯下,或在白色恐怖的囚室角落,用质朴文字传递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。他们坚信共产主义理想终将实现,即便面对生死抉择,仍写下“砍头不要紧,只要主义真”的铿锵誓言。这份信仰,让他们甘愿将个人命运与国家、民族的未来绑定,用生命践行承诺。如今我们翻开这本书,字里行间的信仰之火仍能点燃心中的理想之光:面对工作中的难题、生活中的挑战,这份“认准目标便一往无前”的信念,正是支撑我们前行的精神支柱。
其次是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。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,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。《湖湘红色书信》中,这份初心被具象化为一封封滚烫的信件:1921年春,任弼时致父亲任思度的信中写道“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,同天共乐”,将个人理想融入民族未来;1937年9月18日,即‘九一八’事变六周年之际,左权致叔父左铭三的信中强调“请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、伟大的”,字里行间满是对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。他们将“小我”得失置于“大我”兴亡中考量,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抉择。今天的我们,或许无需面对生死考验,但这份“为他人、为社会贡献力量”的初心,仍可转化为岗位上的尽职尽责、生活中的温暖善意,比如科研工作者攻克技术难关、基层干部扎根乡村服务群众,都是对这份初心的当代践行。
更要学习的,是那份炽热深沉的家国情怀。《湖湘红色书信》中的家国情怀,从不是空洞的口号,而是生死关头的无悔抉择。1928年3月10日,钟志申在致兄长钟志炎、钟志刚的信中,既坦诚对家人的牵挂,又坚定表示:“我所做的事业是伟大的,我的血是不会白流的。我死之后,还有无数的人会为了人类的自由而奋斗。”他深知自己的选择意味着与家人永别,却仍愿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。这份“舍小家为大义”的抉择,让家国情怀有了最动人的注脚。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,家国情怀或许体现在青年人为祖国科技发展刻苦学习,体现在普通人在平凡岗位上为社会添砖加瓦,体现在面对国家需要时“舍小我赴大义”的担当。
《湖湘红色书信》不只是一部红色典籍,更是一部鲜活的思政教材。它让我们看见,革命年代的湖湘儿女如何用信仰照亮前路、用初心坚守方向、用情怀扛起责任。今天的我们,虽身处不同时代,却同样需要这份精神力量。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勇攀高峰,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挥洒汗水,在文化传承的征程中坚守初心,这是我们对革命先辈精神的最好传承。
这部书,是湖湘革命前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。让我们带着这份精神力量,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“实事求是”的品格、秉持“敢为天下先”的勇气,用行动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“红色答卷”,让湖湘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。
>>我要举报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