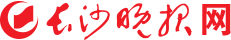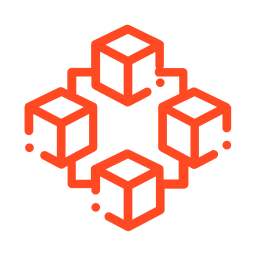兰 痴
易秋鹜
还在母亲腹中时,我就常听见父亲吟唱“兰之猗猗,扬扬其香。不采而佩,于兰何伤。”那调子清得像山涧的小溪,悠悠地绕着屋梁,竟成了催我降生的鼓点——母亲意外摔跤后,我提早两个月来到人间。父亲总说:“我生时虽瘦如弱猫,却带着清雅的香气,是兰托了观音菩萨送来的。”我的人生,就这么被一缕兰香系住了。
儿时的我体弱多病,为了治我的病,父亲翻遍了中医典籍,竟也成了半个医者。一有闲暇,他就带我上山:既可强身健体、采草药,也可去山中访兰。有时刚进谷,满峦的暗香就裹着风扑来,我和父亲总会异口同声:“今天来得真巧!”抬头望去,兰叶凝着晨露、泛着翠色,素白的花苞攒着香气,任溪水叮咚流淌,它自守着一隅清欢。这时父亲会伸出手,轻轻抚过兰叶,那温柔的模样,让我想起夜里我生病难眠时,他也是这样一遍遍抚摸我的脊背。我曾幼稚地拉着他的衣角撒娇:“咱们把它带回家养好不好?”父亲却摸着我的头笑道:“它朝伴晨雾、暮枕流水,早守惯了这方澄澈,我怎忍心把它拽进俗世烟火里?”那时的我似懂非懂,却悄悄记下:山谷溪旁,才是兰最好的家。
可这份与兰相伴的时光,停在了我十六岁那个冬天——父亲走得突然,像一阵风突然吹走了身边的暖意。后来我成了家,孩子的哭闹、柴米油盐的琐碎、生活的手忙脚乱,渐渐磨掉了赏兰的雅致。直到孩子长大,我和母亲在乡里有了自己的蜗居,种兰的念头才又冒了出来。可家乡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:工厂陆续搬来,镇上的居民们不用烧柴,山林长得遮天蔽日密不透风,从前常见的兰,竟再也寻不到踪迹。
一次去同学家做客,听他说云南弟媳的陪嫁里,有十二株金童玉女兜兰——那年头兜兰价格不菲,一株就要近千元。我便缠着去一睹芳容,偏偏没赶上花期,只见到深浅绿相间的网格斑兰叶,层层套叠着像撒娇的孩子。指尖触到硬挺的叶片,那独特的弧度像小耳朵,我忍不住想象它开花的模样,连遗憾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前几年,曾免费住在我家空置房的事实孤儿小柏,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工作。他记着我喜兰,教师节前竟用第一个月工资,买了十二种不同的兰寄来,附言写着:“老师,想圆您的梦,想给您惊喜!”拆开包裹时,四株兜兰先撞进眼里,还有十一种叫不上名字的兰。时隔十年再遇兜兰,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那之后的一周,我去山上捡了腐烂的松树皮和松针,刨了腐殖土,去小溪边淘来小青石,在池塘边捋了十几斤柳叶泡水发酵。最后选了桂花树下和紫藤架下两处风水宝地——既遮阴又通风,最像山林里的环境。夏天高温时,我每天给紫藤和桂树喷两次水,给兰营造湿润的小气候;早晚用千分之一的氮肥和磷酸二氢钾溶液喷洒叶片,一周浇一次柳叶发酵水。终于,在春风里,兰叶渐渐绿得要滴下来,花芽也悄悄钻出了泥土。过年时,春兰先来报恩了——哪里是开花,分明是把一整罐清雅的香揉碎了撒出来,凑近闻是浓得化不开的甜,走远了又缠在鼻尖,连风都软乎乎的。接着是兜兰:“玉女”的花茎直直立着,囊状的唇瓣粉嘟嘟的,犹如面泛桃花、不胜娇羞的少女,头上还戴着一顶吸引昆虫授粉的条纹小帽子。“金童”更可爱,活像揣着小兜兜的“小财童”,连开花都透着要送惊喜的劲儿,真的是兰花界妥妥的颜值担当。
到了盛夏,我以为花儿该歇了,君荷却突然开了,那香气似清风拂面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调制的香水,瞬间扫走了所有燥热。
等白雪皑皑时,报岁兰又吐蕊了。它裹着紫褐色的花瓣,像穿了件古典旗袍,在冬日的萧瑟里独自绽放,打破了冬季的单调与冷寂。
四季有兰相伴,我从没觉得孤单,可心里总像牵着一根线,连着想寻兰的念头。
去年,刚离异的闺蜜邀我去贵州散心,我们选了山间的民宿住。早听说贵州山里多兰,我便想着去寻寻“老友”。下午见闺蜜在房间读《如懿传》,我跟她说去山间走走,她还戏谑地说:“别走远了,小心被山里的精怪掳走!”一进山林,古木参天、烟雾缭绕,潺潺的溪水声绕着林子转,果然是兰的天堂。可走了半天,连兰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我偏不死心——见不到它,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刚要转身,蓦然回首,竟见一丛万代兰在高处枝杈间“招手”。虽错过了花期,可兰叶间冒出了纺锤状蒴果。
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兰的蒴果,这遗憾,我得帮他补上。四周没人,我也顾不得装淑女,三下五除二脱掉裙子和皮鞋,攥着湿滑的青苔,光着脚就爬上了树枝。指尖碰到蒴果的那一刻,像回到了童年——仿佛父亲就在耳边轻声呢喃:“今生无憾了。”此刻,我像是突然握住了父亲递来的手,又像是寻回了丢了多年的念想。
闺蜜找到我时,我还在树上盯着蒴果发呆。她见我衣衫不整,心急地喊:“你这是被抢劫了,还是被非礼了?”我笑着跳下来,来不及穿衣服就笑嘻嘻地回答:“是的,我的灵魂被兰‘绑架’了,连每个细胞都被它‘非礼’了。”
我指着树上的蒴果,想跟她分享这份惊喜,可她瞬间红了眼眶,瘪着嘴,眼泪突然掉下来:“‘兰因絮果’有什么好高兴的?你看我,新婚时像兰花一般芬芳美好、幸福甜蜜,但最终由于丈夫的背叛,像絮果破裂后的飞絮飘忽离散,从此天各一方。”见勾起了她的伤心事,我赶紧抱住她,柔声宽慰:“傻瓜,你只看见絮果会裂,却没看见里面藏着千百粒带薄翅的种子。等蒴果成熟,风一吹,它们就会飞到新的地方,落地就能生根、萌发生长,还会一季一季地盛开。连一粒小小的兰种都敢跟着风儿去闯,我们人,难道还不如它吗?”
其实想想,我这一辈子,不也像兰一样?从父亲身边的“弱猫”,到被生活磨掉雅致的主妇,再到如今守着满院兰的自己,不就是在“兰因”里寻初心,在“絮果”里找新生吗?我对兰的痴,不是痴于它的幽香、它的静美,而是痴于它那份不管在哪儿,都能守住自己、再开一次花的劲儿——这才是“兰痴”最该守的初心啊。
>>我要举报